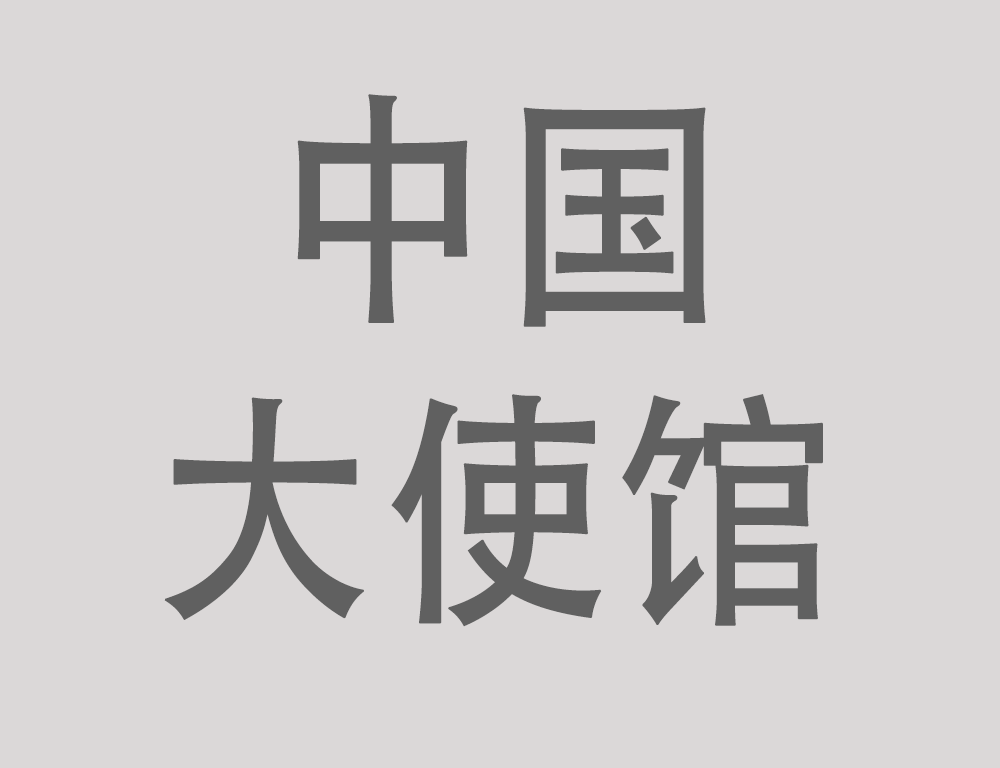望着对方盈眶的泪眼,倾听只有在书里记录过的史实,不由生出别样的感喟:原来上个世纪中期已在新加坡落户两三代的移民,故土情结仍是那么深重!迁居南洋已近十年,每个有着迁居经历的人,都应该明了十年所蕴藏的感慨。之所以不用“旅居”,是身份变了,心也安定了,已然在此地安居乐业。然而,前半生的经历毕竟太多、积淀毕竟太厚、回忆毕竟太深,在天平的一端终究是吃重的。相貌神情是无法同化了,口音谈吐更是难以消弭故国的痕迹,虽然这些事实本来无关荣辱,却也时时被人贴标签、加论断。中国来的?会讲英文吗?在牛车水被人当“陆客”兜售旅游纪念品,在小贩中心又被追问“大姐,来自中国哪里?”虽然对方并无恶意,心头还是涌起一种滋味:尴尬。
尴尬游子心,尴尬的不只是别人如何看自己。随着近些年中国新移民的涌入,北方饭菜于岛国已不再陌生。每当看到喧腾腾的白馒头、大包子,油汪汪的锅饼、凉拌菜,还是忍不住食指大动,大包小包提回家品尝。一番狼吞虎咽之后,又套用土生土长新加坡人惯用的“太油、太咸”来评论。国大、南大校园食堂里的“北京风味”是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字号,不去光顾吧惦记,吃完后又摇头叹气。尴尬的不只是对食物的品味 。某次在樟宜机场排队等候登机,遇到在中国最为普及的“新马泰”旅行团。其中两名面目黝黑、满身异味的男性团员旁若无人地插队,引得被越过的妇女大吼道: “Can’t you see I’m queuing? What the hell!” 语气中透露出忍无可忍的爆发力,被吼的两人因语言不通,也倒泰然自若。夹在两方中间,一面为曾经的同胞不懂规矩而汗颜、羞耻,一面又因如今的新加坡人没有容人之量、爆粗口而忿然。此情此景,怎一个“尴尬”了得?
也听过、见过、勇于甩脱这种夹缝生存状态的例子,感动过也无奈过。有一次在工作间隙,与一名新加坡的同事聊天。他讲起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新加坡华人是如何倾其所有,把大量的食物和日用品通过香港寄给大陆的亲人;60年代中期,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下令关闭设在新加坡的中国银行时,东南亚华侨又是怎样奋力储蓄,使其免于被吞并的命运——这一幕在《从苦力到巨子——李引桐传奇》的描述中得到了印证:“人群里有踏三轮的工人,手中的钱脏兮兮;人群里有公司经理,他们驱车几十、几百公里风尘仆仆;人群里有家庭主妇,手中裹着平日攒下的菜金; 人群里有大学学生,书包内装着前日打工得来的报酬;人群里甚至有未成年的孩子,小手举着平日父母给的零花钱。中国银行保住了,它如今仍高高地耸立在太平洋之滨。”而亲口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人,就是当时把零用钱拿去储蓄拯救中国银行的孩子之一。望着对方盈眶的泪眼,倾听只有在书里记录过的史实,不由生出别样的感喟:原来上个世纪中期已在新加坡落户两三代的移民,故土情结仍是那么深重!另一次在工作场合结识一名年轻女士,递过来的名片上是非常中国化的汉语和新加坡化的方言拼音姓名,开口交谈则是用“新式英语”(Singlish),于是以为碰到的是华语较弱的新加坡同胞。合作挺久之后,才从另一同伴口中得知,这名女士来自中国,而且到新加坡不过七八年。从言谈举止到生活习惯,她早已脱去了故国的影子,融入新加坡了。出于好奇,问及她何以在新加坡年轻一代已普遍采用汉语拼音姓名的今天,要用方言拼写自己的名字,她接二连三地说“无所谓”。其实姓名无非是个符号,然而在新加坡,无论学校老师还是用人单位,都可以通过拼音的方式,轻而易举地判断谁是土生土长的华人,谁是来自神州大地的新移民。不知道这种“无所谓”能否成为摆脱尴尬的挡箭牌?如果能的话,教育、工作场合的先入之见,是否就此可以消解了呢?